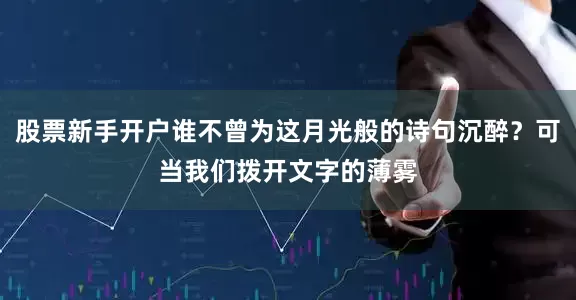
图片
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——这如烟似雾的诗句,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民国文学的星河里。徐志摩笔下的《再别康桥》,用丝绸般柔滑的文字织就了无数读者的文学梦境。初读时,谁不曾为这月光般的诗句沉醉?可当我们拨开文字的薄雾,诗人的真实人生却呈现出更复杂的纹理。
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江南才子,本名章垿,留学英伦时为自己改名志摩,仿佛早已预见未来如云漂泊的命运。从杭州一中的青葱岁月,到剑桥河畔的哲学沉思,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云雀,在东西方文化的天空往返飞翔。新月社的创立、北大讲台上的身影、报刊杂志上的锦绣文章,构筑起他光彩夺目的公众形象。
图片
然而诗人的感情世界却像他笔下的康桥水波,看似平静下暗流汹涌。16岁那年,当兄长带着张幼仪的照片来到徐家,少年志摩那句乡下土包子的评语,已然为这段婚姻埋下伏笔。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,在丈夫眼中却成了封建礼教的化身。即便在剑桥的秋雨中相会,徐志摩眼中看到的也不是身怀六甲的妻子,而是远方的自由幻影。
图片
泰晤士河畔的偶遇改变了故事的走向。林徽因——这个如四月天般明媚的少女,让诗人陷入了疯狂的爱恋。在伦敦的穹顶图书馆,在北京的胡同深处,他像追逐光影的飞蛾,哪怕对方已与梁思成缔结婚约,仍不肯放手。这段无果的痴恋,最终化作《偶然》中那句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,方向。
图片
而陆小曼的出现,则像一剂令人眩晕的香水。北京饭店的舞会上,这位能画善舞的名媛,用沾着唇印的高脚杯接住了诗人破碎的心。他们的爱情像一场华丽的冒险:顶着世俗骂名,耗尽万贯家财。当徐志摩奔波于三所大学拼命授课时,可曾想起当年在康桥写下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的那个自己?
1931年深秋的那场空难,将一切定格在35岁。济南开山的浓雾中,那架邮政飞机坠落的轨迹,恰似诗人一生追求的飞与自由的隐喻。留在世间的,是张幼仪后来创办的云裳服装公司,是林徽因书房里未读完的信笺,是陆小曼卧房中永远等不到主人的烟榻。
重读徐志摩,我们或许该将诗与人分开看待。就像欣赏敦煌壁画不必追问画工生平,沉醉《再别曲》也无需认同诗人的选择。那些飘在云端的诗句是真实的,那些落在尘世的遗憾也是真实的。这大概就是文学与人性最耐人寻味的辩证法——伟大的艺术可以诞生在不完美的人生里,而我们对作品的欣赏,也不必等同于对创作者的全然认同。
图片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网上配资网站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市配资风云这场盛会将打破传统文旅边界
- 下一篇:没有了
![哪些证券公司比较好[3]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鳝的热量](/uploads/allimg/250829/290646140102303.jpg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