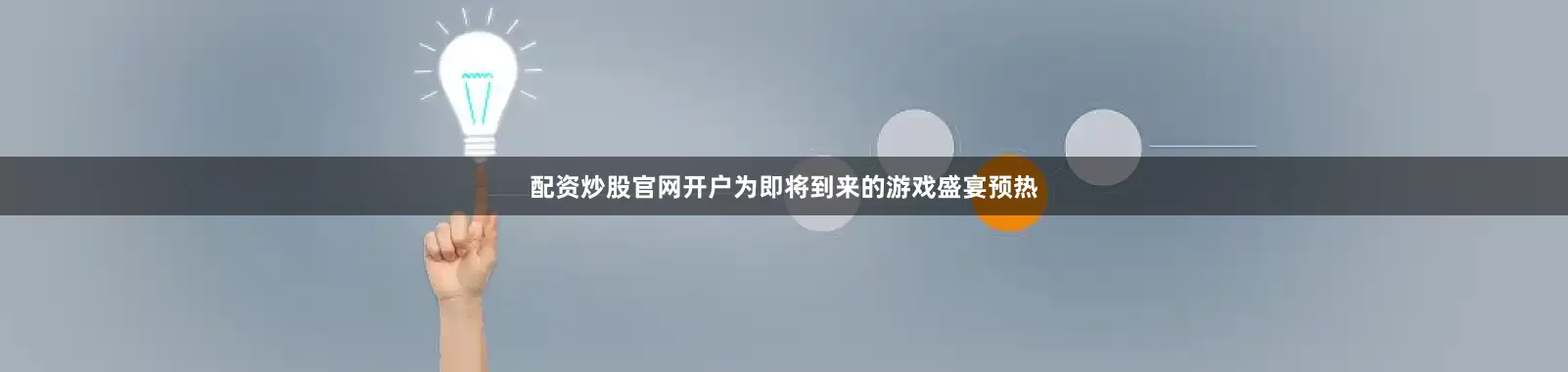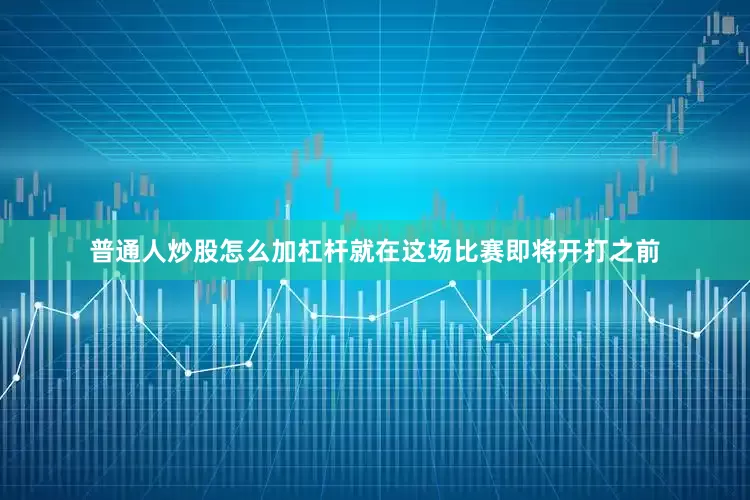烂游戏的瓜千千万,好游戏背后的刀,永远是同一把。
最近总有人在后台问,说某某工作室的核心制作人又被优化了,某某爆款手游的初代主策又“因个人原因”离职了,问我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天大的黑幕。
我说朋友,你格局小了。
这算什么黑幕?这在游戏圈,不叫黑幕,叫“新陈代谢”,叫“历史规律”,叫“文种宿命”。
对,就是那个给勾践献上“伐吴七术”,一手把越国从ICU里捞出来,最后被勾践一剑送走,顺便给后世贡献了“鸟尽弓藏”这个成语的倒霉蛋,文种。
很多人聊文种,总说他蠢,说他看不透勾践那张“可共患难,不可共富贵”的PUA脸,连隔壁同事范蠡都套现离场、带美女主播泛舟五湖去了,他还在那儿算今年新麦的KPI。
这叫蠢吗?
不,这叫路径依赖,这叫沉没成本,这叫一个顶级项目经理,对他亲手拉扯大的项目,爱得深沉。
讲白了,游戏圈里每一个被“优化”掉的功勋制作人,骨子里都是一个想不开的文种。他们不是看不懂版本答案,他们只是放不下自己一行一行码出来的代码,一张一张画出来的原画,和一个一个顶着压力实装上去的系统。
今天,我们就借着两千年前的这把剑,来聊聊游戏圈里,那些永远在重复的“文种之死”。
一、从泥地到版号:制作人的“会稽山之耻”
每个成功的游戏项目,立项之初,都蹲在自己的“会稽山”上。
可能是老板画的一个饼,可能是投资人一个“我全都要”的需求,也可能只是团队凑在小黑屋里,靠着外卖和红牛,憋出来的一个Demo。
这时候的团队,跟当年被夫差按在地上摩擦的勾践没什么两样——缺人,缺钱,缺资源,唯一不缺的,就是“再输一把就解散”的压力。
这时候谁能站出来?
只有文种。
哦不,是那个游戏制作人。
书上说,文种去吴营,把祖传的玉圭按在泥里,对着夫差磕头,说“我们越国愿意全国给你当奴隶”。
这是什么?
这就是制作人拿着那个BUG比功能还多的Demo,去跑发行、找投资的孙子样。
发行方就是夫差,趾高气昂,看着你的项目计划书,就像看一个笑话:“就你这像素风还想做开放世界?今年KPI够吗?首月流水能破亿吗?我们这S级的渠道,凭什么给你?”
制作人能怎么办?他只能把自己的“玉圭”——也就是自己那点可怜的行业履历和创作理想,死死按在心里,脸上堆着笑,对着发行和渠道磕头:“大佬,您说得对,我们这个不行,那个也不行。但您看,我们团队执行力强,特别能熬,996是福报,007是追求。只要您给个机会,给点资源,我们保证当牛做马,数据绝对给您做上来!”
那一刻,制作人的尊严,就跟文种额头上的血一样,不值钱。
他怀里揣着的,不是什么老乡给的麦饼,而是团队几十号兄弟的饭碗,是美术妹子熬夜画的UI,是程序员小哥拿头发换来的底层代码。
这玩意儿,比脸重。
所以他能忍。为了那个该死的版号,为了能让项目活下去,别说磕头,让他学狗叫都行。
二、从内测到公测:粮册上的代码与陶刀般的社区反馈
项目活下来了,勾践被放回了越国,版号下来了,游戏开启了内-删档-不删档-公测的漫漫长征。
这时候,退居二线的“勾践”,也就是老板和投资人,每天的工作就是发表重要讲话,回忆自己当年如何慧眼识珠,顺便畅想一下公司纳斯达克敲钟的盛况。
而真正干活的,是文种。
是那个天天泡在项目里,把公司当家的制作人。
文种在越国搞经济,推行“平粜法”,国家调控粮价,保证老百姓有饭吃。这事儿在游戏里叫什么?
叫数值调控,叫经济系统搭建。
他拿着一摞摞“粮册”,挨家挨户地算收成,这不就是制作人盯着后台数据,看每日新增、看留存、看付费率,一个小数点一个小数点地抠么?
游戏里的“老贵族”——也就是那些只看短期收益的运营和市场,会跳出来拍桌子:“新版本必须加强氪金点!开新卡池!必须把ARPU值拉上去!管他什么平民玩家,他们又不花钱!”
文种怎么说?“公是什么?公是百姓能吃上饭。”
制作人怎么说?“游戏的核心是什么?是玩家能玩得爽。你把平民玩家都逼走了,氪金大佬去割谁的韭菜?这个系统必须改,必须给白嫖玩家留条活路,生态才健康。”
他拿着笔在竹简上写“谷贱增价收,谷贵减价售”,墨迹能透两层。
制作人拿着键盘在策划文档里敲“新增保底机制,调整抽卡概率”,每一个字符背后都是一场和运营部门的血战。
然后,一个老农送了文种一把自己烧的陶刀,说“大夫保住了我们的口粮”。
这就是玩家。
当玩家在论坛里发帖,说“这个版本改得好,终于不用被土豪吊打了,谢谢策划”,或者在TapTap上留下一个五星好评,说“这游戏虽然小众,但能看出制作组的用心”。
那一刻,玩家的认可,就是那把粗糙的“陶刀”。
它不值钱,甚至有点丑,但制作人会把它当宝贝,别在自己腰上,比什么项目奖金、老板画的期权,都贴身。
因为这是他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里,唯一能支撑他没从天台跳下去的东西。他觉得,自己做的一切,值了。
三、从爆款到裁员:桑皮纸的邮件和压在代码下的初心
终于,游戏成了。
就像越国灭了吴国,游戏登顶了畅销榜,流水破了纪录,媒体通稿满天飞,老板在行业峰会上意气风发,大谈特谈自己的“商业哲学”。
庆功宴上,所有人都来敬制作人的酒,说他是“力挽狂澜的英雄”,“游戏圈的文种”。
他可能也喝多了,看着满屋子的香槟和笑脸,恍惚间觉得,这么多年的苦,没白吃。
然后,范蠡的信就来了。
在游戏圈,这封信的名字,叫“猎头的邮件”,或者叫“老同事的私信”。
信上写得明明白白:“兄弟,公司马上要被大厂收购了,或者要开始搞降本增效了,勾践要卸磨杀驴了,赶紧跑路!我这边有个新机会,成立个独立工作室,咱们自己当老板!”
(插一句,这套路在互联网大厂裁员里你见得还少吗?)
文种看着信,看了半宿。
那个被优化前的制作人,也看着那封邮件,或者那个微信聊天框,沉默了半宿。
他不是傻子。
他当然知道,游戏成功之后,自己这个“功高震主”的创始人,就是老板眼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他懂太多核心技术,手下人又都服他,万一哪天带着团队跑了怎么办?
而且,游戏已经进入稳定期,不再需要什么开天辟地的创造力了。公司需要的是听话的、便宜的、能搞“微创新”的螺丝钉,而不是他这种又贵又有想法的“爹”。

换掉他,换个更年轻、更便宜、更听话的“产品经理”,游戏的流水可能短期内都不会有影响。
这笔账,勾B……哦不,老板算得比谁都清楚。
可他为什么不走?
范蠡能走,因为他眼里只有功名利禄,搞定吴国这个项目,他的KPI完成了,拿钱走人,天经地义。
文种为什么不走?
因为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:新收的麦子样本,画了一半的农事规划图,还有那把老农送的陶刀。
制作人为什么不走?
因为他打开电脑,看到的是:下一个版本的更新计划,还没跑通的新玩法代码,还有玩家社区里那个置顶的“BUG反馈与建议收集帖”,里面几千条留言,他都还没看完。
说真的,这事儿就离谱。
一个创造者,最终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给绑架了。
他舍不得。
他觉得,新版本上线,玩家一定会喜欢那个新角色;那个困扰大家半年的BUG,他马上就要找到解决方案了;社区里那个天天提建议的小朋友,他还答应要送他一个周边来着。
“再等半年,等下一个大版本更新完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他把猎头的邮件拖进了垃圾箱,就像文种把范蠡的信压在了粮册底下。
他以为自己守住的是一个项目。
不。
他守住的,只是自己身为一个创造者的执念。一个太过天真的,初心。
然后,勾践的剑就来了。
可能是一封HR的邮件,标题是“关于组织架构调整的通知”;也可能是一场15分钟的会议,没有客套,只有一句“感谢你为公司做出的贡献,但基于业务发展需要……”

那一刻,他接过那把“剑”,就像接过一个等待已久的判决。
他甚至没力气去争辩什么N+1,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,抱着那个印着公司LOGO的纸箱子,走出那栋他曾经以为会奋斗一辈子的写字楼。
他最后摸了摸自己电脑里的代码,那上面有他写的“新功能预计下月实装”,代码还热乎着。
他最后看了一眼玩家社区,首页飘着的还是“感谢制作人,这游戏是我今年玩过最好的游戏”。
剑落下时,他没回头,只是盯着窗外——那里能看到远处的CBD,新的游戏公司,新的制作人,正在上演着和他一模一样的故事。
一个轮回。一个该死的,无法挣脱的轮回。
后人说文种愚蠢,说他不懂“鸟尽弓藏”的职场铁律。
可我们这些玩家,欠了太多“文种”一句谢谢。
我们今天玩到的那些真正好玩的游戏,那些让我们沉浸、让我们感动的虚拟世界,有多少不是靠着这群“愚蠢”的制作人,用自己的肝、用自己的头发、用自己那点可笑的执念,硬生生从资本的獠牙下抠出来的?
他们不是看不清老板的凉薄,只是放不下对玩家的承诺。
他们不是不知道套现离场更潇洒,只是忘不了玩家给他的那把“陶刀”。
他们不是没有机会走,只是舍不得那个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、还不够完美的世界。
这种“不聪明”,恰恰是游戏圈里最稀缺的“人味儿”。这真的很重要。我是说,这事儿真的、真的很重要。
所以,下次当你看到某个功勋制作人“被离职”的新闻时,别急着吃瓜,也别急着骂资本无情——因为骂了也没用。
你只需要记得,曾经有这么一个“文种”,他守着心里的那份“信”,把自己活成了一款游戏的一部分。
然后打开那款游戏,再多玩一会儿。
这,可能就是对一个游戏人,最好的纪念。
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,倡导文明、健康的社会风气。如有内容调整需求,请提供相关证明以便处理。
配资网上配资网站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a股加杠杆他已将B队门将刘琪玮提拔至一线队
- 下一篇:没有了